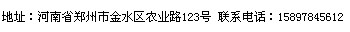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荒野之国拍摄手记1
题记——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准备,为了迎接这过去的五天。念头在春天播种,夏天发芽,终于在秋风与阵雨的丽江交汇。奇怪的城堡,晃动的秋千,细雨中的呼喊。风,雨,人,和奇异的荒野之国,晨雾使得光线变薄,三维的世界变得扁平,荒野里的人,像是在二维的画布里流淌。女孩一说,她经常梦到飞翔。女孩二说,希望有个人替自己看守自己。男一说,他最不能接受的创作就是正常。这是我要讲的故事,是曾经迷恋的「逃离和寻找」,它们相悖,往往又同时存在,逃离是为了寻找,就像告别往往是为了相聚,一场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包围,一个现实与想象、过去与未来的脆弱边界,正在被找寻的路上。我希望TA们有所收获,正如我受益匪浅。一年参加工作,到现在大概21年,目前人生的一半,如果我活到80岁,那么这段时间是我人生的四分之一,——总之,它并不短。21年的时间,我一直努力成为「成熟的采访者、理性的记录者和真诚的观察者」,若不是前几天发生在拍摄现场的事件,我一度以为自己达成所愿了呢——在过去21年的时间里,拍过感人至深的爱情,也拍过英雄失势的落魄,拍过委屈,拍过冤枉,拍过离别,更拍过相逢,拍过被误解,拍过被攻讦,也拍过极度的欢喜,和同样程度的悲伤……总之,各种可能引起失控的强情绪事件,没有一千,也有八百——拍摄现场失控,几乎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。但是,一万个没有想到。在一个所谓的“真人秀”面前,在众多工作人员环绕的场景下,在两个大概21岁的女孩背后,在那个普通得不值一提的夜晚,在那个微风小雨的束河,我的情绪如雪崩般坍塌,猝不及防,逃不掉、甩不脱、摆脱不了。这么的吧,一句话就是:在拍摄的时候,我突然哭了。不但哭了,而且是控制不住的哭。要是默默流泪也就罢了,我不但哭出了声音,而且还倒在人家家里的地板上哭。那是一种极其清醒,明知不可以却无法停止的哭泣。我清醒的知道,刚刚有感觉的时候,摄影师翰宾给我拍了一张照片。接着是胸腔开始不对,发出一种奇怪的,别人未必听得到,录音师张楠肯定有察觉异样的声音(后来果然是这样)。「录音师小楠楠,作品等身,《隐秘的角落》录音指导」声音出来后,想要捂嘴控制一下,但是情绪已经起来了,抽刀断水,是没有用的。于是干脆躺倒在现场的地板上,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,打扰他们的工作,到底头都是打扰我自己的工作,我得敬业。见鬼!不行!控制不住!不知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——家里的自来水没水了,但是管子里还存着一点点余量的时候——打开龙头,便会发出一种“呲呲、扑扑、呲呲”的声音。我是想说,我的哭声一定很难听,我的喉咙里发出的正是缺水的水龙头被打开的那种呲呲扑扑——它是没有水——我呢,并不是停水了,管子里有水,但得残酷的压抑着。事后复盘,摄影师这边,首先是摄影指导少光发现我的异样,他把惊讶和疑惑的眼神递给了他对面的摄影师乾军,乾军接下这份疑惑,马上闪送给二楼平台我身边的摄影师铁彬,铁彬心领神会,立马放弃了他盯拍的艺人,饶有兴趣的把镜头对着了我——这是一场安静而默契的眼神交汇和接力,发生在一瞬间,他们拍片时经常这么干。「就是这三个人咯」平时在电影院,感动感动湿湿眼眶也就算了,在看书时,即有泪从脸上滑过,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——因为私密的环境,你不用去在意它,更不用去控制它,这次哭泣让我深刻的意识到——眼泪是止不住的。哭泣也是止不住的。「抹一把眼泪,继续看着现场,是不是很敬业?」长久时间以来,不太熟悉眼泪和哭泣,事到临到头,想到突然控制住,是不可能的——凡事都是熟能生巧——太久不哭了,既无法预知它的到来,更不知道怎么收场。真是一个糟糕的现场。我于是放弃了现场拍摄,哭出声来,然后上了二楼,心想楼下的兄弟们,你们继续拍吧,爱咋拍咋拍,爱拍啥拍啥,你们开心就好——我得先哭一会儿。赵琦后来幸灾乐祸地说(这么写是需要,他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人):不错哦,还没有丢掉感动的能力。二这次导致我哭泣的是三个罪魁祸首:一个中年人的破吉他和破心事;一个年轻人的致命大提琴;另一个年轻人的秘密;第一个吉他和歌声,直给,像攻坚般的入侵,有点难以抵档;第二个大提琴,像随风潜入的小雨,也像锦衣夜行的鬼,它会占据你的每个毛孔;第三个是秘密,也是共情,是这次我失控的根本原因。现在我离开这三个罪魁祸首了,我也不再怕TA们弄我了,我可以无所顾忌的点名了:祸首第一位:乔小刀。如果不是他把我弄哭了,我会这样介绍他:一个平易的艺术家,黝黑的瘦子,永不停歇的狂想者,跑位飘忽的劳动者,同时还是一个因为省钱而锻炼出来的手工能力大师,不按牌理出牌的搅局者,秩序的破坏者,常规的敌人,总之,是一个充满着诱惑与不确定的创作者;现在看来,他显然是一个“坏人”。唱民谣就算了,他的歌词撩起人来不分男女。另一位帮凶,比乔小刀更“邪恶”。年轻的大提琴演奏者,别人家的女儿,人格四分的复合体,音乐的精灵,结构主义者,逻辑大师,“懂事”的大人——这是我对她的描述,欧阳娜娜——AB型的双子。双子座最著名的原型来自希腊神话中的一对同胞兄弟,一个是神,一个是人,凡人会死,神却不会,哥哥愿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,换取弟弟的复活,他们的父亲答应了这个请求,交换生死,兄弟两人轮流活一天,一个人在天堂,另一人在冥府,如此交换,如此循环……这个略带悲伤的故事,也许说明着双子为什么有时候明亮,有时候孤寂,看上去最简单的星座,却有着最复杂的一面——有多开心,就有与之对应的悲伤,有多热闹,就有可能与之对应的冷清,就像光与影的二元性相伴,双子的娜娜或许有过感知吧,这是宿命,是她的喜悦之地,也是孤独之源。扯远了,她的琴声是我倒下的直接原因——我挡得住六指琴魔,挡得住莫大先生,甚至可以挡一挡曲洋刘正风,但是在现实中,我倒在这个家门小姑娘的琴声之下,古龙说,漂亮的女人最不可信,是真理。第三位祸首,是知道别人的心事。怎么描述她呢?她是阴郁的阳光,是快乐的眼泪,是温柔的刀子,是敏感的迟钝,是坚强的脆弱,是乐观的悲观——这都是矛盾的病句,但放在她身上,不是。不但不是,而且我觉得她或许也能同意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体,而我私下其实挺希望她能成为《箫十一郎》中的风四娘,或者《边城浪子》中丁灵琳那样的女性,没跟她说过,但她可能看得到。她说越长大越孤独。其实谁不是呢,十一种孤独,能够囊括我们天下所有人。还有更孤独的呢,姑娘,我曾死死的记住过一段对话,是李寻欢与阿飞之间的:
“你看,这棵树上的梅花已开了。”
“嗯。”“你可知道已开了多少朵?”“十七朵。”李寻欢的心沉落了下去,笑容也已冻结。因为他数过梅花。他了解一个人在数梅花时,是多么孤独。
她就是那个年轻的演员,易遥、清平乐里的公主、如果拉一个最值得期待的年轻女演员榜单,里面绝对会有她的名字——任敏。
三那天晚上,在乔小刀的烂吉他和娜娜的大提琴下夹击下,任敏首先沦陷了,她从沙发上,慢慢滑落到地上,埋头不语。中年男人乔小刀的粗糙嗓音,钻到人的耳里,心里,钻出门缝,钻进雨夜,在丽江的晚风中飘荡,“Howmanyroadsmustamanwalkdown,Beforetheycallhimaman”,不是这首歌,但大概是这个情境,这个意思,这份心情。娜娜的大提琴声如影随行,不让人喘息,虽然她是即兴应和,在我看来,她这是即兴杀人。当时我还想,看欧阳娜娜拉琴,还不花钱,多好的四儿啊。没想到她以琴声杀人,还不见血。任敏受不了。我完全百分百的知道为什么任敏受不了。所以我就非常受不了任敏的埋头低涰的背影。而这个知道的背后,是我和她共享着一个秘密,一份心事。她没有说,我就更加不好说。歌声作妖,琴声作崇。小刀和娜娜在无意中击倒了任敏。我知道任敏为何而倒却不能言说,所以我也被干倒。要不然,这点琴声,这点歌声,算什么。就是这么个事儿。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。飞机上睡不着而已。以上,是为序。真正的拍摄过程,是他们三人带来的丰富体验:放飞的思绪,彼此的探索,失真的场景,穿越云霄的大笑,泪流满面的痛哭……我曾对娱乐圈抱有偏见,现在我依然认为那是一个巨大的酱缸,但是只要你对「人」不抱有偏见,就一定会从将来的片子有所感触,我们都是人,读那么多书的许知远先生,五年以来以那种姿态去与各种人交流,说是带着偏见看世界,其实他做的是在消解偏见的樊篱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呢。希望有时间能接着写完这个拍摄手记。虽然有一堆更务实的破事迎面而来。白天结束拍摄后和小刀、赵琦聊天,我说我想生活在魏晋,但是竹林七贤好几个都入了仕啊。妈的。晚安,未眠的人们。晚安,赐予我哭泣的三大“祸首”。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